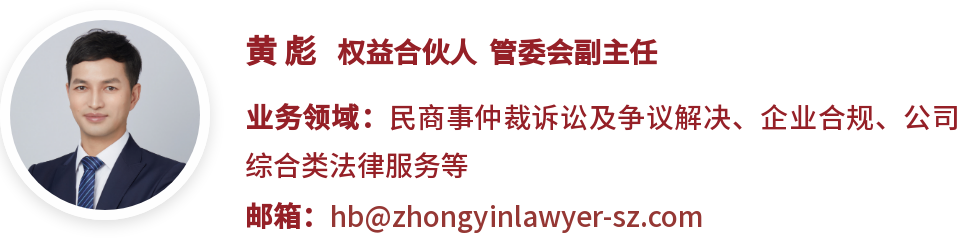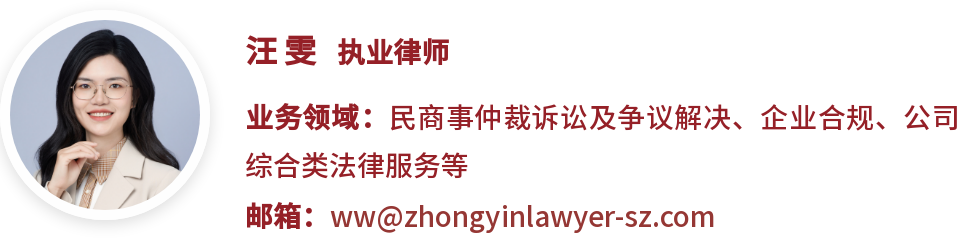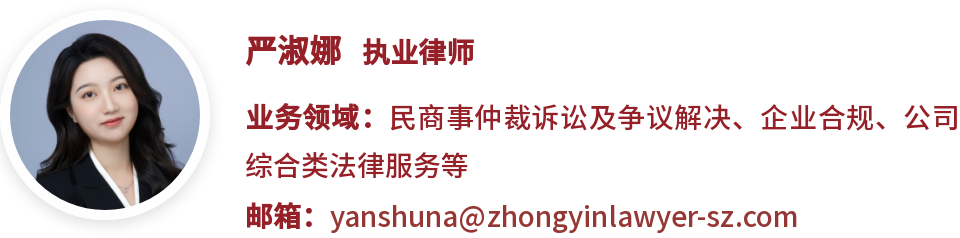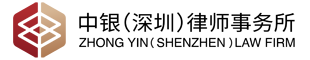引 言
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网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等提供了线上平台。与此同时,区别于传统交易方式,以信息网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方式也应运而生。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新增了通过信息网络订立买卖合同的合同履行地的补充规定。
同时,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巨大便利,通过淘宝、京东、微信、供应商云平台等各类信息网络方式的交易越来越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越来越多,“信息网络方式”的种类也愈发具有多样性,这也导致了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激增。然而,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该类案件的管辖认定存在不同的观点。
本文将从传统交易方式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本文特指常见的、以动产为交易对象的买卖合同纠纷,不包括有特殊管辖规定的买卖合同纠纷)的地域管辖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地域管辖规定、法律适用规则等方面对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进行梳理、探讨。
一、传统交易方式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
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又以当事人是否有协议约定管辖作为标准进行了区分。
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此,基于上述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况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同时,基于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对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民事诉讼法同样赋予了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一审管辖法院的程序性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如当事人之间已约定选择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且不违背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首先按其约定确定管辖法院。
二、“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地域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一)什么是“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
1. 对“信息网络”的界定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对何为“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做出统一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就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条款编著的书籍对此提供了部分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2022年6月版,第116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2015年3月版,第159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逐条适用解析》(杜万华、胡云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2015年3月版,第28页)均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规定》)中第二条对“信息网络”的界定,即“信息网络”是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并认为审判实践中可以参照该“信息网络”的概念,认为通过上述媒介订立的买卖合同,均可视为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
然而,对于上述观点,司法实践中在就个案是否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进行审查时,部分法官持有不同的观点。
例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辖终90号案。该案的观点是《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信息网络”的定义,仅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民事纠纷案件,并不包括基于信息网络买卖合同产生纠纷的案件。《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关于“信息网络”的概念不应等同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二者在保护法益、立法旨趣等方面相距甚远。《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侧重于保护在信息网络虚拟不确定的情况下买受人权益受损时的程序利益,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管辖规则具有倾向性保护的特点,为维护商事交易的平等秩序,其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制。买卖合同的“信息网络方式订立”需要满足“特定网络平台”+“平台上发布、展示商品”+“交易在平台上完成”的要件,即在特定的电子商务平台面向不特定消费者发布、展示产品,完成交易。如果只是将微信等作为协商的工具或者合同文本内容转发对方的载体和方式,该情形不具备信息网络方式订立合同的特征。
笔者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相关书籍对判断个案是否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作出了相应的指引,但其也仅是认为“可以参照”《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规定》第二条中“信息网络”的概念对个案进行认定。然而,基于以互联网飞速发展导致的以信息网络方式形成的交易的多样性、复杂性,司法实践中不应机械地套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规定》第二条的概念,应当根据个案的实际交易情况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判断,以避免出现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
2. 司法实践中对于常见的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的类型认定
(1)通过淘宝、京东等特定的电子商务平台交易形成的买卖合同
随着电商行业、网络直播的发展与兴起,通过淘宝等特定电子商务平台形成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类案件性质的认定较为统一。其中,部分法院的裁判观点摘录如下:
(2023)甘民辖77号案中,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将标的物在互联网等信息平台上展示并发出要求,买受人通过信息网络作出购买承诺,双方形成合意而订立的买卖合同。根据原告牛某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本案系因互联网购物引发的纠纷,属于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原告牛某主张其通过被告新某的服务平台、以支付对价的方式从被告吴某处购买游戏账号后,被游戏账号原出售方即被告王某修改密码,导致其丧失对游戏账号的使用权,原告牛某遂针对游戏账号出售主体、交易平台、游戏开发主体提起诉讼。”
(2024)苏02民辖终138号案中,案涉交易系通过抖音商城进行,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该案系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
(2024)粤01民辖终249号案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通过闲鱼网络购物平台及微信交流,订购案涉车辆,约定通过货运配送,收货地为广州市增城区,故案涉买卖合同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
(2022)京04民辖终25号案中,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裴俊涛通过淘宝网与东莞市大朗佳酿酒业商行签订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
综上,当前司法实践中,通过淘宝、京东等特定电子商务平台与不特定消费者之间产生的交易,因具备通过虚拟网络平台发出要约、作出承诺并最终达成合意的特征,通常会被认定为“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
(2)通过微信等通讯软件进行沟通、磋商、交易而形成的买卖合同
微信、QQ等通讯软件带来的便利性使得通过微信等进行沟通、磋商、进而形成交易越来越多。然而,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通过微信等沟通、交易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均被认定为“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需要结合个案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其中,部分法院的裁判观点摘录如下,可作为参考:
(2023)最高法民辖66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合同是否可以认定为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本案中,周志豪起诉主张其与泽航公司以微信聊天方式买卖货物,但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对周志豪所作的调查笔录记载,周志豪与泽航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林在案涉买卖发生前相识,周志豪到泽航公司处考察后,吴林通过微信向周志豪报货单,周志豪依货单送货。此后,周志豪还到泽航公司处催要货款。从案涉买卖过程看,买卖双方明确且相互知晓,微信仅是双方沟通方式之一,案涉买卖合同的要约、承诺等订立行为并非全部通过微信方式达成,故不宜认定为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应当按照一般合同纠纷确定管辖。
(2023)最高法民辖14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合同是否可以认定为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本案中,王有朋主张其与俞文权达成了黄沙买卖合同,并向开发区法院提交了其与俞文权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未就案涉买卖签订书面合同,微信内容主要为双方就合同履行以及发生履行争议后的沟通情况,微信内容同时显示双方亦曾面谈。可见,微信只是王有朋与俞文权的沟通方式之一,案涉买卖合同并非双方通过微信方式订立。故案涉合同不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普通的买卖合同。
(2023)京02民辖终90号案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信息网络买卖合同交易主体具有虚拟性的特征,对该合同认定的范围不宜扩大,应仅限于具有典型信息网络合同特征的“网络购物行为”,微信只是双方传达合同内容的载体和方式,不具备信息网络合同的典型特征。……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辅以微信等方式对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确认,符合交易习惯及经济效益,不能仅以通过微信方式进行了沟通、协商就认定双方之间达成的内容属于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同时,《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侧重于保护在信息网络虚拟不确定的情况下买受人权益受损时的程序利益。如果将微信上订立的买卖合同一概纳入“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范围,从而确定买受人住所地或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则明显造成程序上的不公正,特别是当出卖人主张支付货款时,其往往只能到买受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将极大增加维权成本。另外,买卖合同的“信息网络方式订立”需要满足“特定网络平台”+“平台上发布、展示商品”+“交易在平台上完成”的要件,即在特定的电子商务平台面向不特定消费者发布、展示产品,完成交易。如果双方只是将微信作为协商的工具或者合同文本内容转发对方的载体和方式,则此情形不具有信息网络合同的特征。”此外,对于上述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2024)辽14民辖终20号案中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持有该观点。
(2024)冀06民辖终56号案中,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以微信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是否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应当结合实际情况予以认定。信息网络买卖合同交易主体具有虚拟性的特征,对该合同认定的范围不易扩大,应仅限于具有典型信息网络合同特征的“网络购物行为”。本案中,微信只是双方传达合同的载体和方式,并不具备信息网络合同的典型特征,因此上诉人主张按照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缺乏事实依据。
(2024)粤05民辖终9号案中,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将标的物在互联网等信息平台上展示并发出要约,买受人通过信息网络作出购买承诺,双方形成合意而订立的买卖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所规定的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管辖权划分情形,其宗旨是在买受人接受产品的终端不具有确定性以及出售方出售产品的终端不确定的情况下,解决网购消费者难维权以及管辖法院不明确的问题,本案中,在案证据显示双方当事人系将微信作为双方交易时磋商的工具,以微信方式商讨合同细节、传输合同内容,交易主体是特定的,且买受人及出卖人的终端也都是确定的,据此达成的交易不符合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与一般买卖合同并无差异,应当以一般买卖合同纠纷确定管辖。
(2024)苏02民辖终14号案中,上诉人主张“其是通过微信向林某购买布料、匹数等,林某通过微信报价,其表示无异议后便通过微信把收货地址发送给林某(陆某),其通过微信向林某支付了货款,林某通知物流方发货,整个交易过程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在此买卖之前双方并不相识,故该买卖合同属于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对此,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林某主张其与段某达成了买卖合同,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虽未就案涉买卖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就货物买卖的标的、数量、价款、交货方式等的协商均已在微信中约定,故双方成立“线上订立、线下交货”的买卖合同关系,应以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综上,根据案例检索情况可知,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通过微信等以通讯功能为主的软件形成的交易,需要结合个案的交易过程、细节等进行综合判断。整体而言,如通过微信等成立的买卖合同同时符合“特定网络平台”、“平台上发布、展示商品”、“交易在平台上完成”的要件(或是通过虚拟网络平台完成发出要约、作出承诺并达成合意的),通常可以被认定为系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而那些仅仅是通过微信聊天等方式就交易细节等进行沟通的,往往被认定为不具备“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特征。
(二)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合同履行地的区分
通过信息网络订立买卖合同的合同履行地的补充规定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以信息网络方式进行的交易激增的经济背景下而新增设立的,是为解决因信息网络方式交易存在虚拟、不确定等特点而易导致的被告住所地通常难以被直接知晓、合同履行地难以确认等问题。因此,该条款实际上是在特定情况下针对买受人的倾向性保护,通过对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作出明确的规定,侧重保护在信息网络虚拟、不确定的情况下买受人合法权益受损时的程序利益。
同时,考虑到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交付方式的多样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对不同形式的买卖合同的履行地进行区分,即: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而对于上述两种交易的区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逐条适用解析》(杜万华、胡云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2015年3月出版,第27页)对此进行了说明:“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形式为“线上交易、线上交付”,即线上交付数字化产品,如在电脑或者智能手机上购买并下载应用程序软件等数字化产品等,该类合同的履行地为“买受人住所地”;关于“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交易形式,即指“线上交易、线下交付”,该类产品主要是实物产品,而实物产品不像数字化产品那样通过信息网络交付而难以确定收货地址,因此将“收货地”规定为该类合同的履行地。
同时,基于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该补充规定依旧强调了当事人约定优先的原则,也即“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三、传统买卖合同纠纷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之地域管辖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
如前所述,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实际履行但没有约定的履行地点的买卖合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传统买卖合同纠纷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的合同履行地存在着不同规定。具体来说:
对于传统买卖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十八条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而对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因此,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作为一种新形式的买卖合同,在确定其合同履行地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法律规则适用竞合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不同法官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与第二十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法院因此对该类案件的管辖认定存在着不同的裁判结果,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法律适用规则。
而对于该特定情况下的法律适用,笔者认为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已对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的合同履行地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该特别规定应当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一般合同纠纷的合同履行地的一般规定优先适用。因此,在根据合同履行地确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法院时,应当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以减少法律适用的差异,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以便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保护自身的程序利益。
四、结语
综合上述,不同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于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的认定均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因此,在诉讼过程中,基于不同的诉讼地位、诉讼目的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原被告双方均可能做出不同的诉讼选择。具体而言,原告在起诉时应当慎重选择起诉的法院,避免出现法院不予受理或是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后被法院裁定移送的情况,由此造成诉讼进程的拖延;相反,被告在答辩期限内应当关注受诉法院有无管辖权、有无提出管辖权异议之必要,在特定情况下可减少诉讼成本的增加等。
律师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