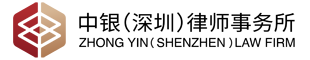引 言
区块链技术催生的虚拟货币,以其去中心化、匿名性与跨境流通的特性,在重塑金融格局的同时,也为犯罪活动开辟了新的“隐秘通道”。从利用比特币、以太坊(Ethereum)、泰达币(USTD)进行毒品交易、勒索赎金,到层出不穷的交易所盗币、代币发行诈骗、跨链桥洗钱,虚拟货币犯罪呈现出技术性强、隐蔽性高、跨境化广的新态势,这类犯罪对传统刑事法律框架构成严峻挑战。本文将立足实务,分多期剖析我国虚拟货币犯罪司法实践现状,探讨破局之道。
一、我国对虚拟货币的态度
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曾于2021年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此外,《通知》还明确了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服务,即提供任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的都不是合法的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
然而,由于《通知》仅属于规范性文件,且无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虚拟货币进行规制,导致现阶段对涉虚拟货币行为是否均为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存在较大争议。
二、仅买卖虚拟货币是否有刑事犯罪风险?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体系尚未对虚拟货币设立专门罪名,其法律定性主要依托于对现有刑法条文的体系化解释。从目前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为了投资,仅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若相关行为触碰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同样将会面临刑事制裁。
在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中,单纯买卖虚拟货币行为被认定为犯罪的情形呈现以下典型特征:
(一)上游犯罪关联性:当购买虚拟货币的资金来源非法,或出售的虚拟货币来源非法,买卖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可能符合“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移财产”等客观要件,易被认定为洗钱罪、帮信罪、掩隐罪等。
(二)交易对象特殊性:与黑心币商进行交易,买卖双方自行议价成交,平台无法监管,涉及“黑钱”的风险较高。
(三)交易方式异常性:线下现金交易因存在匿名性、不可追溯性等特征,易被认定为掩盖犯罪行为的手段,被推定具有犯罪故意。
三、涉虚拟货币犯罪类型
这类犯罪直接围绕着虚拟货币的特性展开,虚拟货币或其代表的“价值”是犯罪侵害的直接客体。
1. 盗窃罪
尽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具有很高的安全性,但也可能被黑客通过技术手段攻击交易所或平台,盗取用户的虚拟货币。
2. 敲诈勒索罪
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和不可逆性使其成为勒索者的首选支付方式,追踪和追回难度大。
3. 行受贿犯罪
行贿者向受贿者直接转移虚拟货币,作为行贿款项。这种新型贿赂方式方式更隐蔽,难以留下传统银行转账记录。
(二)以虚拟货币作为犯罪工具/手段
这类犯罪的核心目标是实施传统犯罪,虚拟货币因其特性被犯罪分子选为更隐蔽、更高效的“工具”或“支付通道”。
1. 诈骗罪
如“杀猪盘”投资诈骗,诱导受害者在虚假交易平台投资虚拟货币,最终无法提现,或冒充官方客服诈骗,以“账户异常”等理由,骗取用户私钥或诱导转账等。
2. 非法集资类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
未经批准,通过发行虚拟货币、代币、或以投资虚拟货币挖矿、交易、理财项目等名义,承诺保本付息或高额回报,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3.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以发行虚拟货币、推广区块链项目为名,要求参与者以虚拟货币形式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
4.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洗钱罪
(1)“跑分”:为上游犯罪提供资金通道,利用个人或控制的账户接收赃款(虚拟货币),通过买卖、兑换等方式进行混淆转移,从中赚取佣金;
(2)“提供OTC交易服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仍为其提供虚拟货币兑换法币的场外交易服务;
(3)“提供技术/账户支持”:为犯罪活动提供虚拟货币钱包、交易所账户、混币服务等。
5. 非法经营罪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开展虚拟货币兑换、变相买卖外汇、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业务活动。
6. 赌博罪/开设赌场罪
如在线赌博平台接受虚拟货币作为赌资和下注筹码;或利用区块链技术直接构建去中心化赌博应用。
上述罪名的行为模式、风险识别及司法认定中的关键要点,笔者将在后续的实务文章中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
四、刑事案件中虚拟货币价值认定争议
(一)价值认定争议
目前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虽已被否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其“财产属性”仍然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属于刑法保护的“财物”。然而,在涉及虚拟货币犯罪案件中,如何认定行为人的犯罪金额,各个认定依据之间存在较大争议,各个法院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认定结果。现有的认定方式及相关案例如下:
一是以犯罪行为发生时该虚拟货币的市场价格为标准。
案例一:(2021)豫04刑终483号案件,法院认为:“涉案的以太坊币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可以交易、转换成实际的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且代币平台每天都会公布交易价格,公诉机关以犯罪时涉案以太坊币交易价格认定本案的犯罪金额并无不当。”
二是以被害人所受损失为标准。
案例二:(2022)苏04刑终210号案件(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裁判理由提到:周某平购买泰达币的交易记录系有效价格证明,可按照被害人遭受的实际财产损失的数额确定诈骗数额。
三是以虚拟货币处置变现后的金额(即销赃金额)为标准。
案例三:(2020)沪0106刑初551号案件,法院认为:“我国不认可任何虚拟货币交易价格信息发布平台对于虚拟货币的交易价格数据,故不应当认定涉案泰达币根据相关网站的历史价格计算。考虑到罗**将泰达币兑换以太坊后,又将以太坊兑换人民币,实际获利约90万元,可以参考相关司法解释,根据销赃数额认定盗窃数额。”
四是以价格鉴定机构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为标准。
案例四:(2024)豫0823刑初436号案件中,经武陟县价格认定结论认定:2021年10月15日一个欧意虚拟货币(泰达币)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6.4322元;2022年2月9日一个欧意虚拟货币(泰达币)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6.3717元。被告人孟*非法转移的75000个USDT虚拟货币(泰达币)总价值为人民币480297.5元。该法院认可了机构所做的价格认定结论,并以此作为计算依据。
(二)律师辩护策略
由于虚拟货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价值波动大以及交易方式复杂多样等独特属性,这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乃至不同司法人员对于虚拟货币犯罪金额的计算和认定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等有失公平的情况发生。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律师在开展辩护工作时,应当将核心焦点聚焦于对控方所主张的犯罪金额计算方法进行深度剖析与有力质疑。律师需要仔细审查控方计算方法的每一个环节,从数据来源的可靠性、计算方式的合理性等多个维度,全面且深入地指出其不合理之处。
律师应积极主动地引导法院采纳对当事人最为有利的犯罪金额认定标准,也就是金额最低的认定标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律师需要充分论证该标准在结合虚拟货币特性和具体案件情境下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附上能够支持辩护意见的相关裁判案例,最大程度上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 律师结语
面对虚拟货币犯罪这一新兴领域的挑战,律师要以专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在办理案件时,需深入研究虚拟货币的技术特性、交易模式以及在案件中的具体作用,精准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并密切关注各地法院的裁判倾向和典型案例,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灵活选择对当事人最有利的价值认定标准进行辩护。
律师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