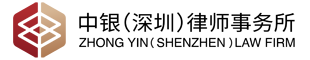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系在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领域耕耘十余年的高景贺律师[1]对2007年—2019年代表性案例所进行的系统梳理和实务分析,因文章内容丰富详实,文字较多,故分为系列文推送,本文为第一篇,主要涉及植物新品种案件中的诉讼主体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路径。后期精彩内容请关注深圳中银律师事务所公众号。
相对于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业务,植物新品种案件属于知识产权实务中相对“冷门”的板块,植物新品种案件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也未能获得足够的关注。司法案例中体现出的审判思路以及法院对争议问题的阐明也没有引起重视。作为在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耕耘十余年的专业律师,分析司法实务中的相关问题,既是“事实与规范之间穿梭往返”的职业习惯的使然,也是“促进育种创新、推动种业发展”的行业使命的召唤。本文基于植物新品种案件诉讼实务的逻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出台后的代表性案例(2007—2019),对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以期能见抛砖之效,助力植物新品种的司法保护。
一、植物新品种案件中的诉讼主体(谁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第7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39条均规定,品种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实务中对于诉讼主体的争议多集中于对品种权人及其利害关系的认定上。品种权人,指的是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职务育种、委托育种、合作育种以及品种权转让中都涉及到品种权人的认定。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2]
1、职务育种新品种申请权属于单位,申请获批后申请人为品种权人
在姚某与山西屯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纠纷案中,[3]再审申请人姚某主张涉案植物新品种“屯玉808”不属于职务育种。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称最高法院)认为姚某作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研发管理、三级试验、新品种审定和引进,还曾任屯玉公司经营农业技术开发的北京生物技术研究院的负责人。屯玉公司不仅给姚峰发放月工资,而且还向姚峰支付育种经费、繁育亲本等费用。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书》中记载的涉案品种的亲本来源和选育过程,亦印证了屯玉公司在涉案育种培育期间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基于姚某在屯玉公司任职期间的工作内容以及屯玉公司为涉案育种培育提供的物质条件情况下,最高法院依《条例》第七条规定认定涉案植物品种“屯玉808”属于姚某为执行单位任务完成的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应当属于该单位。
2、委托育种品种权归属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的归受托人
在前案中,尽管双方签订的《技术合作协议》名称不是育种协议,但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明确载明了姚某提供自交系育种材料、屯玉公司给予补偿和提供选育费用,并享有申请植物新品种的权利等权利义务关系。最高法院认为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应当将本协议视为育种协议以确定品种权申请人。
3、合作育种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的归育种人共有
我国《种子法》和《条例》并没有像《专利法》那样在规定了合作发明创造的归属之后又明确专利共有人的权利行使规则,[4]进而导致在实务中对品种权共有人能否单独许可他人生产销售并授权他人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提起诉讼存有争议。在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大京九种业有限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中,[5]最高法院认为,当植物新品种权存在两个以上权利主体,共有权人对权利的行使存在约定时,应当从其约定。品种权共有人黄某与武威农科院约定由武威农科院单独行使品种权并享有诉权,而武威农科院又许可敦煌种业公司生产经营并授权其可以单独就侵害“吉祥1号”品种权的行为提起诉讼。虽然武威农科院许可敦煌种业公司生产经营时,保留了被许可人武科公司以及武威甘鑫物种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权,敦煌种业公司实际上属于“吉祥1号”品种权的普通被许可人,但在武威农科院予以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敦煌种业公司作为“吉祥1号”植物新品种权的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有权提起侵权诉讼。不同许可类型的起诉主体有所区别,但获得明确授权的情形下,要结合具体情况判断。
此外,在合作育种中,仅提供资金帮助无权获得共有人身份。共有品种权人应按约定行使权利,如无约定,可以自己实施或者普通许可他人实施,未经共有人同意不能排他或独占许可他人实施,也不能转让品种权。
4、独资企业注销后的合法继承人继受植物品种权
《司法解释》界定利害关系人包括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对于独资企业,其投资人对其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权利,故可以认定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为其合法继承人。在绥化市天昊种子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北方稻作研究所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中,[6]最高法院认为,涉案植物新品种权人的原权利人绥化市北方稻作综合研究所是乔某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该企业已于2008年注销。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乔某礼对其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权利,故乔某礼对涉案植物新品种权享有合法权益,北方研究所根据乔文礼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有权对涉案植物新品种权进行维权,提起本案诉讼。
二、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路径(怎么诉)
1、植物品种权保护和专利保护
对于植物品种以及与植物品种有关的发明,具体的保护路径存在着区分。美国对植物品种给予植物专利和植物品种权的重叠保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0年首次在Diamond v. Chakrabarty判例中承认微生物可以授予专利。[7] 1970年美国开始提供品种权保护,但仅针对有性繁殖或者茎块繁殖的植物,不包括杂交品种,[8]但直到2018年通过对《农场法案》(Farm Bill)的修订,美国才对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提供品种权保护。[9]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1年针对AG Supply, Inc. v. 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 Inc.的判决进一步确认美国以植物专利、实用专利、植物品种保护法三种方式保障育种者权利的体制。[10]
欧盟对于植物品种则严格规定只能通过品种权保护,但是对于与植物有关的发明,符合专利授予条件的,则可以获得专利权保护。欧洲专利公约(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EPC)第53条(b)款明确排除了动植物品种,生产动植物的生物学方法的专利性。[11] 1998年颁布的《欧盟生物技术发明保护指令》第4条除了重复EPC对于动植物品种专利性的限制外,在第2款中还规定了技术可行性不限于特定的植物或者动物品种的植物或者动物的发明可以授予专利。[12]欧洲专利局内设的扩大上诉委员会在2015年西兰花II[13]和西红柿II[14]的上诉案件中指出,通过实质生物学生产的植物或者植物材料,如果不是特定的植物品种,那么其可以授予专利。
我国对生产植物品种的方法给予专利保护。(2013)高行终字第1972号“一种利用两系法培育亚种间杂交稻组合的方法”的发明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江苏农科院请求保护的是一种利用籼粳中间型不育系培矮64S作母本,以籼稻9311作父本配制杂交种的培育方法。[15] 另外,中国还出现了创世纪种业起诉山东圣丰种业侵害“两种编码杀虫蛋白质基因和双价融合表达载体及其应用”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创世纪种业请求法院依法指定检测机构对涉案产品“山农圣棉1号”棉花种子进行基因序列检测,比对检测到的转基因序列与涉案发明专利保护的基因表达序列是否相同。该案涉及到基因专利保护范围是否直接延伸至棉花种子理论探讨。[16]
2、商标及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保护
(1)通过商标专用权保护植物新品种。品种权名称因具有区别品种能力、识别育种者身份等功能而具有商业标识属性,授权品名与商标权本质上存在暗合之处,故可以通过商标权实现对品种权的间接保护。[17] 授权品名用于区别品种,商标用以区别商品来源。[18] 两者虽有交叉,但并不能对应替代,同一品种可划分为多个商标。如郑单958最初由四家种子企业经营,分别使用秋乐、金娃娃、金博士、德农四个商标,后又增加中种集团经营,使用中字牌商标。同一商标也可以经营多个品种,如联创商标下就有中科玉505、裕丰303、联创808等三个系列。
(2)通过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品种名称可以经过广泛使用取得显著特征,进而与相关产品产生特定的联系,构成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进而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在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诉王某某、山东新天隆种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中科四号牌鲁单981”种子的不正当纠纷案中,[19]“中科4号”作为农业部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载明的品名经过持续使用,具备了识别商品来源、区分商品质量的功能,属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依法应受到保护。又如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江苏省泗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和销售白皮包装小麦种子过程中使用“宁麦13”名称的不正当纠纷案中,[20] 法院认为,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品种繁殖材料与其品种权名称之间系双向唯一对应关系。侵权人以白皮包装和以被授权品种名称对外销售相关植物新品种时,即使所销售并非被授权品种,仍会造成购买者误认为是被授权品种,故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亦对植物新品种权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3、通过商业秘密保护植物新品种
除了专利保护和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路径外,通过商业秘密对植物品种进行保护的路径常常被忽视。商业秘密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可以涉及育种、生产、储存、销售等四个环节,特别是育种环节的亲本的选择、育种方案和实施技术等内容,最能发挥商业秘密的作用。[21] 有观点认为对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特别是杂交亲本材料应是合理的取得,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否则可能会被以侵犯商业秘密罪提起诉讼。[22] 但实务中对于亲本繁殖材料能否获得商业秘密保护存在不同认识。以先玉335亲本繁殖材料为例,权利人曾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请求相关部门撤销使用先玉335亲本繁殖材料的杂交种审定或暂缓审定以及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等,而其之前代理律师在南方农村报公开称很难将先玉335的亲本材料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由此可见,可通过商业秘密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
4、中国商业秘密保护品种权的最新案例
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中国司法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研究之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以商业秘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例,但尚未引起行业足够的关注。在(2019)鄂05知刑初2号案中,[23] 公诉机关指控覃某盗取康某公司的玉米亲本并使用涉嫌商业秘密犯罪,法院认为,康某公司的技术秘密主要是指公司植物新品种原始材料、中间材料、自交系与亲本,其载体主要是涉及公司上述技术秘密的文字记录、摄影录像资料,其保密措施主要体现为:康某公司设有专门的亲本仓库和专门的亲本管理人员,亲本进出仓库都有严格的登记,亲本杂交技术、配方是康某公司的核心技术秘密并经康某公司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康某公司的玉米亲本、杂交技术和康某20、高某909玉米杂交种具有重大商业价值,能给康某公司创造财富,是康某公司的无形资产。覃某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利用工作之便,秘密窃取康某公司玉米种子繁育的核心玉米亲本产品和核心杂交技术,提供给他人,并亲自指导他人秘密生产康某公司受保护的玉米新品种,以换取高额的报酬,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康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公诉机关指控覃某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由此可见,在实践中对植物新品种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保护已经存在,实务中应转变思维方式,以最优方式实现对育种人利益的保护。
注释:
[1] 高景贺律师,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银深圳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本文首先感谢审判一线法官的专业和敬业使得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研究素材,其次感谢团队的助理鞠枭磊、杨玉枝、王纯、杜洁惠等人帮助搜集国内外案例和整理校对文稿,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
[3] (2017)最高法民申1801号,合议庭:周翔、罗霞、佟姝,2017年6月21日
[4]《专利法》第15条规定:“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5](2014)民申字第52号民事裁定,合议庭:周翔、罗霞、周云川,2014年5月21日
[6] (2019)最高法民申2061号民事裁定,合议庭:杜微科、吴蓉、张玲玲,2019年6月27日
[7] U.S. Supreme Court. Diamond v. Chakrabarty, 447 U.S. 303 (1980)
[8] 李菊丹: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第63页
[9]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Under the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1/06/2019-27636/regulations-and-procedures-under-the-plant-variety-protection-act)访问日期:2020年5月25日
[10] J. E. M. Ag Supply, Inc. v. 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 Inc., 534 U.S. 124 (2001)
[11]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Article 53(b)
[12] Directive 98/4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ly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Article 4(2)
[13]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G 0002/12 of 25.3.2015
[14]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G 0002/13 of 25.3.2015
[15] (2013)高行终字第1972号,合议庭:刘晓军、袁相军、马军,2013年12月30日
[16](2012)济民三初字第144号,合议庭:李玉、李现光、刘军生,2014年7月14日
[17] 侯仰坤、王雨本:不同法律方式保护蔬菜新品种的比较,载《中国蔬菜》2010年第3期
[18] 臧宝清:植物新品种名称能否注册为商标,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年11月20日
[19](2010)皖民三终字第00001号,合议庭:余听波、王怀正、张坤,2010年2月4日
[20](2018)苏民终1527号,合议庭:何永宏、刘莉、汤茂仁,2018年12月12日
[21] 侯仰坤:植物新品种权保护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5月,第275-276页
[22] 刘振伟、余欣荣、张建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导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97页
[23] (2019)鄂05知刑初2号,合议庭:刘乾华、黄孝平、罗娟,2019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