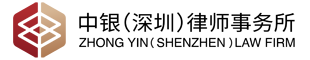相对于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业务,植物新品种案件属于知识产权实务中相对“冷门”的板块,植物新品种案件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也未能获得足够的关注。司法案例中体现出的审判思路以及法院对争议问题的阐明也没有引起重视。高景贺律师作为在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耕耘十余年的专业律师,分析司法实务中的相关问题,既是因“事实与规范之间穿梭往返”的职业习惯的使然,也是因“促进育种创新、推动种业发展”的行业使命的召唤。本文基于植物新品种案件诉讼实务的逻辑,结合2007年品种权司法解释出台后的代表性案例,对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以期能见抛砖之效,助力植物新品种的司法保护。文章内容较多,分为系列文推送,本次推送为第二篇,主要涉及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后期精彩内容请关注深圳中银律师事务所公众号。往期系列文章请点击文末相关链接。
三、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诉什么)
1、UPOV公约对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界定
一直以来,国际上对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界定就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收获材料(包括使用繁殖材料获得的整株植物和植物的部分),植物本身以及为嫁接和繁殖新植物而被切断的枝条、接穗,都应当作为繁殖材料给予保护;也有人认为,应包括植物的任何材料等。UPOV公约78文本中将品种权的保护范围限定在“有性或无性繁殖材料”和“无性繁殖材料应包括植物整株”两个方面。[1] UPOV公约91文本则将由繁殖材料延伸至了收获材料及直接制成品。[2]
2、我国对品种权保护范围的讨论
对于我国品种权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界定涉及科学技术理论问题,不是司法机关单独所能解决的,但就某些记载新品种特异性的授权机关的书面审査材料,在与授权机关达成共识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先行解释作为侵权判定的证据使用。[3]还有观点认为,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应当是授权品种的特异性。[4]《司法解释》征求意见时,林业和农业的主管部门也有不同意见,前者认为应以审批机关批准的品种权申请文件记载的特异性为保护范围,而后者则主张申请品种的全部遗传特性都包含在繁殖材料中,应以繁殖材料来确定品种权保护范围。[5]《司法解释》初稿也曾经基于专利权与品种权最为接近的考虑,拟借鉴专利侵权的认定方法,但因植物品种是活体,以繁殖材料为载体的生物遗传特性难以用文字全面、准确地描述,无法清楚地划定品种权的效力范围,故无法采用专利侵权判定的“三步走”方法,[6]司法解释最终以被控侵权繁殖材料与授权品种具有相同特征特性作为比对标准进行侵权认定,而并未直接规定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什么。[7]
3、司法实践对品种名称权的探索
一般认为植物新品种权属于创造性智力成果。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是具备生命自繁特征的东西,[8]繁殖材料是植物生命遗传信息的自然表达。[9]新品种的植物生命遗传特性体现在繁殖材料上,品种侵权聚焦在授权繁材上。[10]品种权名称仅是获得授权的前提条件、维持品种的存续要素和品种管控手段,但品种名称并未包含在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内,成为品种权的一部分。[11]然而,立法上,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与品种权名称实现了有机统一。[12]UPOV 公约和《种子法》均规定,品种权名称用于识别品种,[13]在不同品种之间,品种权名称具有唯一性——相同近似品种品名应相区别;在不同阶段(时期),品种权名称具有同一性——审定、授权、登记、推广、销售同一;在时空范围上,载体(繁殖材料)与指代(品种权名称)上具有统一性;[14]在具体使用上,品种权名称与其他标记连用时具有突出性——与商标连用时要突出品名。[15]实务中,权利人实际支配和控制着繁殖材料和品种名称的两个部分的利用,[16]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往往涉及繁殖材料和品种名称两个部分。[17]因品种权名称传递着新品种的种质特性、信誉和育种者身份等信息,[18]品种权名称成为品种侵权核心方式和重要环节。[19]实践中,非法利用品种权名称经营获利的纠纷频发且样式繁杂,从“曾用名销售”[20]到“变名销售”,[21]再到“品名商标化销售”,[22]甚至“数字简称销售”不一而足,“一品多名、一名多品”[23]现象似成为假冒侵权套牌等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泛滥的直接根源。[24]为解决前述问题,开始有了通过品种权名称保护品种权的路径探索。典型代表为河南高院裁定“因品种权名称被不正当使用而请求判令被告停止相应的侵权行为并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属于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移送至郑州法院审理[25]以及审判法官发表的品种名称保护系列文章。[26]
4、我国有关品种权保护范围的最新案例
我国司法实践从未停止对于品种权保护范围界定的探索。在蔡某光、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中,[27]最高院认为,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与繁殖材料密切相关,繁殖材料目前作为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品种权人行使独占权的基础。将品种的繁殖材料规定为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因为品种的遗传特性包含在品种的繁殖材料中。繁殖材料在形成新个体的过程中进行品种的繁衍,传递了品种的特征特性,遗传信息通过繁殖材料实现了代代相传,表达了明显有别于在申请书提交之时已知的其他品种的特性,并且经过繁殖后其特征特性未变。虽然繁殖材料包括有性繁殖材料和无性繁殖材料,植物或植物体的一部分均有可能成为繁殖材料,但其是否属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有赖于所涉植物体繁殖出的植物的一部分或整个植物的新的个体,是否具有与该授权品种相同的特征特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应当以品种权法律制度为基础进行分析。[28]
5、认定繁殖材料的考量因素
(1)在界定繁殖材料的范围时,品种实际栽培时采用的与产品定价相符的常规繁殖技术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使用特殊的繁殖方式,比如采用组培、细胞培养等手段时,其成本是否能够支撑商品利润,是否能够在实际生产中大范围应用,应当是繁殖材料的范围界定时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29]
(2)繁殖材料因植物品种的不同呈现出形态差异。农业品种前者主要指可繁殖植物的种植材料或植物体的其他部分,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以有性繁殖的大田作物居多;林业品种主要是指整株植物(包括苗木)、种子(包括根、茎、叶、花、果实等)以及构成植物体的任何部分(包括组织、细胞),以无性繁殖的园艺花卉、果树林木为主。
(3)杂交种的繁殖材料并不是杂交种本身,而是其亲本(父本和母本)。杂交种是通过不同亲本 (父本 、母本 )经过特定的组合方式得到的第一子代(F1),其第二子代(F2)会发生遗传变异,在特征特性上与杂交种都有不同,且杂交种本身不具有育种学上的可繁殖性,故“杂交种繁殖材料就是F1代杂交种的种子,而不是用于培育杂交种品种的亲本(包括父本和母本)”观点[30]并不可取。
(4)植物品种涉及的材料分为繁殖材料、收获材料以及直接由收获材料制成的产品。作为目前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应当是具有繁殖能力的活体,且能够繁殖出与授权品种具有相同的特征特性的新个体。授权品种的保护范围不受限于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采取的特定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当不同于授权阶段繁殖材料的植物体已为育种者所普遍使用时,该种植材料应当作为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31]
注释:
[1] UPOV Convention(1978 Act), Article 5
[2] UPOV Convention(1999 Act), Article 14(2)
[3] 刘军生:植物新品种纠纷司法实践中的若干问题,载《电子知识产权》2004年第10期
[4] 郝力、胡雪莹: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的问题,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期
[5] 蒋志培、李剑、罗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知识产权审判指导》2006年第2辑
[6] 李剑: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基本问题辨析,载《人民司法(应用)》2008年第7期
[7] 罗霞: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相关思考,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7期
[8] 牟萍:植物品种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4-15页
[9] 侯仰坤:论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10] 李剑:植物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11] 臧宝清:植物新品种权名称能否注册为商标,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 年11 月20 日第007 版
[12] 高景贺:植物新品种品种权名称司法保护研究,载《河南科技》2017年第12期
[13]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第13条第2款、1991年文本第20条第2款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7条
[15]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第13条第8款、1991年文本第20条第8款
[16] 李菊丹: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67页
[17] 张志伟、高景贺:论植物新品种名称权的设定——品种权的二元属性视角,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7年第11期
[18]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第13条第2款、1991年文本第20条第2款。
[19] 侯仰坤:论植物新品种权名称的特征和法律作用,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9期
[20] (2013)皖民三终字第00035号,合议庭:陶恒河、王玉圣、郑霞,2013年6月26日。本案中,“冀优1号”是“冀玉10号”玉米新品种的生产试验时的代号,徐春英销售的玉米品种的外包装上标注“冀优1号”,可以认定“冀优1号”和“冀玉10号”实为同一玉米品种
[21] (2009)郑民三初字第440号,合议庭:赵磊、王富强、梁晓征,2009年9月26日。本案中,被告销售人员出具品种为“中4号”的质量保证卡。
[22] (2010)一中民初字第11841号,合议庭:毛天鹏、李冰青、佟姝,2011年3月22日。本案中,“长玉19”系审定和授权谷子新品种,罗某某申请注册“奥利长玉19”商标,并许可冠海公司经营包装标有“奥利长玉19”文字的谷子产品,《种子销售凭证》中“品种”栏显示为“奥利长玉19(鲁单203)”,《种子销售代理合同》中“品种”栏显示亦为“奥利长玉19(鲁单203)
[23] 李瑞云、林祥明:关于农作物品种名称的思考,载《中国种业》2009年第12期
[24] 刘镇伟、余欣荣、张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导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第93页
[25](2009)豫法民三终字第04号、(2009)豫法民三终字第13号、(2009)豫法民三终字第17号、(2009)豫法民三终字第18号
[26] 王富强、马静:植物新品种假冒侵权行为分析,载《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22期。王富强:植物新品种名称应受法律保护,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4期。李晓昱、王富强:植物新品种侵权判定热点问题探析,载《中国审判》第2011年第4期。
[27](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合议庭:周翔、罗霞、焦彦,2019年12月10日
[28] 周翔、罗霞、贠璇: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确定,载《人民司法(应用)》2020年第1期
[29] 狄强、谢湘:关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条例中繁殖材料范围界定的讨论,载《科学导报·学术》2019 年第19期
[30] 李菊丹:“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的标杆案件,载《中国种业》2020年第1期
[3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19)》摘要,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5831.html,访问日期2020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