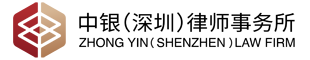近日,针对深圳地区某用人单位因疫情导致停工停产后,在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只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而其他按月发放的津贴不予发放,是否违法的问题,引发关注与讨论。从2020年1月疫情爆发以来,关于企业停工期间,其中有关发放“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如何认定,是实务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笔者拟结合相关讨论,就了解的相关主要实务观点进行概要梳理汇总,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做一简要分析,仅供参考。
观点一认为:按月发放的津贴依法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该项津贴,除浮动的奖金等可以不发放外,如果是固定工资的构成项目,应按照《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28条的规定发放停工工资,即:“非因员工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员工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员工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为止。”
观点二认为: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20]38号,下简称《解答》)的规定和精神,只要发放劳动合同中填写的工资金额即可,主张有相关经办案例佐证。如果按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0条的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既然停工时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就是按“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那么在《解答》第6条第3款以及第14条当中无必要特别明确在第一个支付周期内“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据了解,《解答》的出台背景,旨在为疫情期间不能正常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减负。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解答》对于“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和“按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适用情形有所区别,对于需要特殊保护的群体(如患者、疑似、密接、携带)等,《解答》第5条依然要求“按照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支付”,以及产假、医疗期、工伤职业病等特殊员工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期间的正常工资或相关待遇,《解答》意见之所以在用词上进行如此区分,目的就是区别开需要特殊保护群体和其他非特情员工停工待遇的差别。
观点三认为:《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4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是指员工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为用人单位提供正常劳动应得的劳动报酬。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包括加班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条件下的补助以及按照规定不属于工资的其他费用。 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由用人单位和员工按照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劳动合同中依法约定,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得低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指引》第61条也有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奖金、津贴、补贴等项目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从其约定”。可见,深圳地区司法实践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津贴等项目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该约定受到司法认可;如果没约定,那就未必当然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同时,实践中“津贴”一词很多单位在不同的场合、指代不同的待遇,如果未能判断“津贴”的性质属于特殊工作条件下的补助,那么还要通过双方的约定来确定它是否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范围。如果合同没有约定,需要参考用人单位过往给员工发的每月工资结构。如果该等津贴是每月只要正常出勤就会发放、相对固定,即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一部分;如果是有时候发、有时候不发,或者浮动的,基于特殊原因才会支付的“津贴”,则不属于。即结合观点一,还需要综合考虑该津贴的性质或发放条件、规律、合同有无特殊排除约定等,来判断是否应当纳入停工后第一个支付工资周期的工资标准。
就笔者个人而言,较为赞同观点三。笔者认为,该《解答》发布于2020年4月21日,当时正直新冠疫情爆发后仍然较为严重的时期,其出台背景确实为稳定劳动关系、减轻企业负担之目的,即便观点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此解读适用的相关情形或可能性,但具体司法实践时仍然需要考虑具体情况。特别是随着疫情常态化,稳定和谐劳动关系需要多元出发,同时兼顾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实践不能也不会脱离法律法规的既有明文规定,否则也可能引发有关工资拖欠特别是加班工资、绩效工资、被迫解除等相关的大量劳动纠纷,亦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稳定,因此笔者认为司法实践需要更加慎重的处理该情形下工资标准的认定。
笔者认为,除需要特殊保护的群体应从严适用法律法规外(患者、疑似、密接、携带、产假、医疗期、工伤等特殊员工),因政府管控或疫情影响导致停工停产的工资待遇,如不能通过居家办公或其他方式提供劳动,也无法重新协商新的工资标准或者协商劳动关系变动等情况下,需要慎重理解《解答》中的:未超过一个支付周期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尤其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并尽可能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区别和谨慎理解适用。
需要注意的是,劳动部早在1994年就颁布且至今有效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其第12条中就规定有“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如果将这里的“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等同于“劳动合同文本”记载的具体金额,显然与既有司法实践和法律法规冲突。另外,1994年尚处于公有制经济型企业为主的时代,如国企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一般就是实际发放的标准。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发展、国企改制的加速推进和深化改革,市场主体逐步多元化,出现大量私营、民营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规避法律风险,通常会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较低的工资数额甚至最低工资标准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但并非是劳动者的实际正常工资。在劳动部的暂行规定未及时修改的情况下,大量地方法规在后续制定出台过程中,通过完善和严谨表述回应了时代变化。此后的司法实践中,往往也不能避开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的审查。特别是,2020年1月2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中仍然沿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2条“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的表述,广东省的《解答》又未尝不是与人社部通知保持表述一致。
笔者认为,实践中“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标准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按观点二的说法将《解答》中“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当然等同于“劳动合同文本约定”的工资数额,实际也不具有可行性。具体而言:
情形一:劳动合同文本仅约定了“工资”或者“基本工资“的具体金额或者前述金额等于最低工资数额。笔者认为,此时需要考虑劳动合同文本签署的时间和实践履行中是否对工资标准、工资结构进行了其他书面形式的调整,或者虽未进行书面确认但已经口头变更并实际履行了新的工资标准、工资结构等情况。例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2018年签署了最后一份至今仍在合同期的书面合同或者无固定期限合同,当时合同文本记载的工资数额假设是2200元,但是后续合同履行中工资已经涨到3000元,只要劳动者有证据证明其现在与单位约定的工资数额,理应以此作为“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而不能直接以当时合同记载金额或者仅支付最低工资。再如,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其现在与单位约定的工资结构并不仅限于“基本工资”,还有其他按月固定发放的津贴项目,笔者认为此时除了具有浮动性质、非按月固定发放或者特别约定不属于正常工资、需要满足特定条件等情况才发放的项目可以不发放外,该按月固定发放的津贴项目仍然应计入当前“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来计算第一个停工周期的工资标准。
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需要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规定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司法实践普遍存在事实合同和口头变更合同的情况,司法解释也明确口头变更在实际履行中形成的效力。因此,《解答》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理应包括后续变更后形成的具有薪酬调整或变动的文件,甚至口头变更并实际履行的事实合同,只要劳动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前述工资情况,即应予以支持。事实上,经检索,(2020)粤0391民初8356号案例可支持笔者观点,本案中法院通过审查工资表确定员工的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其中基本工资为同期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公司此后对薪酬数额进行了调整,庭审中公司对此进行了确认。在此种情况下,法院依然以调整后的工资结构和数额作为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并根据《解答》第6条判令公司按照该工资标准补足该停工周期的工资差额,公司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情形二:劳动合同文本并未明确约定工资数额,而是约定工资结构或者仅是约定按照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此时更需要结合工资结构以及单位相关薪酬制度来确定具体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例如,假设劳动合同或公司薪酬制度规定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岗位津贴+餐补+绩效奖金等。同理,无特殊情况和约定排除时,其他按月固定发放的项目当然是“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而不能直接推定劳动合同文本约定不明,跳过工资结构或薪酬制度的审查,采用最低工资标准作为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停工工资。
情形三:劳动合同文本约定了基本工资/正常工资/工资,并明确了具体金额或者等于最低工资数额,但其他项目均是如绩效、奖金等需要按照双方约定或者公司规章制度、在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才能享有等情形。若双方一直如此执行,此后也从未就工资标准或结构进行明确调整或实质变更,或者劳动者无法举证证明前述变更,而停工停产导致不能满足这些项目的发放条件时,此时第一个支付周期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笔者认为在不低于最低工资数额的前提下才能等同于劳动合同文本记载的金额。而这类情形,实际也多出现在工资结构为最低工资/基本工资+加班工资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其他类似以绩效、浮动奖金为主的中小型、小微型、效益为主型企业。此时,在司法审查中根据《解答》意见的精神在审查其“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上给与一定的容忍,笔者认为才符合《解答》的具体精神。通过案例检索,如(2021)粤03民终11113号案例中,有关受疫情影响停工第一个周期内的工资,本案一审法院甚至严格审查了该劳动者的工资结构要求公司补发期间工资,并未采信公司关于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底薪2200元+业绩工资的主张。
情形四: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文本,根本就不存在“劳动合同文本”记载的工资金额。显然,此时必须要去审查具体的工资构成和工资标准,司法裁判不能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文本,而直接推定适用最低工资标准。如(2020)粤0307民初29200号案件中,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对工资结构和标准主张不一,员工主张月工资12000元,公司主张按项目获得报酬,有关受疫情影响停工第一个周期内的工资,法院以用人单位未提交证据证明劳动者的工资结构,而劳动者主张的月工资与银行流水发放情况基本吻合,采信其称的月工资数额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主张,支持了劳动者的相应周期内的停工工资差额。
总体来说,笔者通过公开文书平台检索到的深圳地区的有限案例中,对于停工第一个周期的工资标准,大部分案例会审核具体的工资结构,确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后进行裁判。当然,亦有查到个别公开的裁判文书是按照合同上所载的数额或者最低工资金额进行裁判,但相关文书上就具体关联事实和证据情况记载不明,笔者不便明确引用。前述案例主要是以劳动者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一笔带过。笔者初步推测,可能合同写了基本工资或最低工资金额,而其他工资可能是非固定发放或者劳动者没证据证明系固定发放的情况,或者我理解的工资结构不明或有争议时,依据《解答》精神对单位一方未进行严格审查的情形。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劳动争议的司法实践确实存在较强的政策导向性、裁判不确定性,这一点在处理具体实务案例时需要谨慎注意、把握。
综上,笔者认为,该深圳企业如确因疫情导致停工停产,在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只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而不发放其他按月发放的津贴,如该津贴属于固定项目,且未特别约定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或未附加特定领取条件时,其不予发放该津贴的行为,涉嫌违法。建议相关企业谨慎理解和适用《解答》意见,尽量与员工通过协商新的工资标准或妥善处理此种情形下的薪酬结构、劳动关系变动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