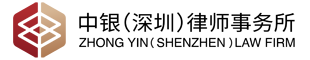侵权人致无近亲属的受害人死亡,“赔偿权利人”是否仅限于“近亲属”及其合理性浅析
关键词:无近亲属 赔偿权利人 侵权后果 公序良俗
近日,与同行讨论一起案例,简要案情:受害人原是一名长期流浪乞讨的精神病患者,近年因交通事故死亡,死亡时无近亲属,但有一名热心人A收留并照顾受害人近15年(未办理收养登记等手续),A将其视为家庭成员般照顾、一直共同生活。受害人死亡后,侵权人赔付了A医疗、丧葬费用,但以A非近亲属为由,认为无义务向A支付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本案争议点:A是否有权作为赔偿权利人,起诉要求侵权人赔付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经过初步讨论和案例检索,总的来说,目前法规规定不明,司法实践就此问题争议较大。
观点一认为:A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其一,现行法律规定“近亲属”有权作为“赔偿权利人”请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而A不属于法定“近亲属”范围,其作为诉讼主体提出诉请无法律依据支持。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亦规定:“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A与受害人不符合相关收养之规定,无法归入前述“近亲属”之列,因此,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如2023年1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裁定(案号:(2022)京民申6188号):该案一审、二审以付某作为受害人的叔叔,不是法律适格主体为由,驳回请求。付某不服申请再审,其主张受害人幼时因父母离异,随父生活,其父因无能力扶养,其作为叔叔,长期由其资助照管付某,特别是受害人生前因腿部残疾被送至养老院生活,费用均系其支付,双方已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受害人死亡后的一切善后事宜也是由其负责。其主张,如仅因自己非受害人近亲属为由,便不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相当于变相地免除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于法不公。北京高院同样以付某非近亲属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请。
其二,有关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已经明确规定,仅有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有权作为“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的死亡受害人的诉讼主体,A目前不属于前述范围。而且,如果侵权人自愿向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支付死亡赔偿金后,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保险公司追偿的,法院不予支持,即保险公司无需赔付该笔款项。如2020年9月14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起再审裁定(案号:(2020)皖民申3584号):该案中,侵权人驾驶再审申请人黄某所有的车辆,致受害人蒋某死亡,蒋某无近亲属,侵权人一次性支付给受害人堂兄弟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车辆损失费等共计14万元,后黄某作为车辆所有人报险,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付被拒,法院即据前述规定驳回了黄某诉请。
对于侵权人来说,此种情况下,既没有明文法律依据支持,又没有保险分担责任,一旦自愿承担后又无法得到保险赔付,便难有主动支付死亡赔偿金的动力。那么,长此以往,是否有利于鼓励好人好事、亲友互助?是否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对受害人、侵权人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来说,这是否合理?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否对等,法律后果是否匹配行为后果?笔者觉得值得探讨和思考。
观点二则认为:前述规定均未讨论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对受害人形成了实质上的抚养、扶养、赡养等关系情况下,是否有权作为诉讼主体的问题。在没有规定的法律空白处,应当以人情常理、公序良俗做填补。因此,对于此类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情况,“赔偿权利人”不应局限于法定“近亲属”或者“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综合本案,A照管患有精神疾病的受害人近15年,与本案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支持相关请求,方符合人之常理和公序良俗。
显然,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我认为,赔偿权利人范围不应局限于“近亲属”,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和扩大“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的范围,并期待司法、立法层面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具体而言:
其一,当被侵权人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时,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就此提出诉请,应重点考察其是否与受害人形成了实质上的抚养、扶养、赡养、扶助等关系,双方是否在精神上相互抚慰、生活中相互扶助、家庭财产相互混同,是否有紧密的情感连接、经济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便有权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如不符合方不予支持。如2020年10月29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案(案号:(2020)甘民申1725号),本案中受害人康某是再审申请人汤某舅舅,该案虽未支持再审申请人汤某请求,但理由是:康某生前无其他近亲属,在事故发生时仅54岁、身体健康无残疾、在外打工有固定的收入,汤某比康某还大四岁,康某在打工闲暇之余到汤某家小住,不能认定对康某形成抚养或者赡养的关系,因此驳回再审申请。重点考查的是双方有无形成实质抚养或者赡养关系,并非直接以其不是“近亲属”予以驳回。
再如,成都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中(来源:人民法院报,详见图片),法官认为:郑某虽不是死者的近亲属,但作为履行了主要扶养义务的实际扶养人,其获得物质的补偿和抚慰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亦尊崇了公序良俗和敬老扶弱的社会传统道德。故赔偿请求权人不应局限于遗产继承人,本案中实际扶养人应有赔偿权利人的资格。

(来源:人民法院报)
其二,应进一步明确和扩大“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的范围。2020年1月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判决(案号:(2019)粤民再240号):本案中,郑某驾车致无名氏和杨某死亡,交警认定:郑某负主要责任,无名氏负次要责任。郑某依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无名氏死亡赔偿金交付告知书》的要求,向东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缴纳483086.4元死亡赔偿金。保险公司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无法定授权,仅是代为保管该款项,郑某未得到被侵权人亲属的代理授权,郑某缴纳483086.4元是自愿行为,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关于“侵权人以已向民政部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等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支付死亡赔偿金为由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等为由拒绝赔付。该案终审采纳保险公司主张,驳回郑某请求。广东高院再审后予以改判,一是以郑某除购买交强险外,还购买了商业三者险,前述规定和观点并未免除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进行赔付的责任。二是“广东省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是根据财政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卫生部、农业部等国务院行政管理部委要求、按照各省市当地实际情况由各省市人民政府制订实施细则、为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利益而设立的公益性机构,其作为代为保存无名死者的死亡赔偿金的机构有法律授权,由其代为保存无名死者的死亡赔偿金有法可依”,视为郑某已履行向无名氏近亲属履行赔偿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分别对郑某缴纳的无名氏死亡赔偿金予以赔付。可见,该案例显然与前述最高院的适用理解一书持不同观点,对于本案中的”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有更为公正合理的理解。
其三,笔者亦认为,即便有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其主张顺位也应次于形成实质上的抚养、扶养、赡养、扶助等关系的其他非近亲属的“赔偿权利人”,如侵权人先行向法律授权的机关或组织赔付相关款项后,后者有权要求前述机关或组织交付代存的款项。
法律常有空白、漏洞,一经颁布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前瞻性、局限性问题,往往容易出现与社会现状脱节、不符人情常理之处。
从法律后果而言,对于侵权人而言,无论受害人有无近亲属,侵权行为都应该具有同等或对等的法律后果,如果因受害人无近亲属就可以免除相关侵权行为责任,或者承担责任后被认为是自愿行为保险就拒赔,那么显然,侵犯生命的后果和代价是不对等的。即便是完全无亲无故的无名氏,也应该由国家机关或有关组织出面追究侵权人责任,使侵权后果与法律后果相匹配,所得款项再用于社会救助与帮扶。
从现实和情理角度里,对于无近亲属的孤寡老幼病残弱,如果其他亲友、热心人、社区组织、福利院等,基于良善、帮扶和公益之心,为此类受害人提供长期照管,自古至今均应倡导鼓励。此类行为尊崇了公序良俗和敬老扶弱的社会传统道德,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和贡献,不能因法律空白、漏洞以及局限性,使其在此类情况下,在经济和精神利益上受损。未来,随着少子化、老年化、不婚不育趋势,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后面很多代人,到一定程度就是无子无女无父无母,届时有亲朋好友、小姐妹小伙伴等愿意为自己提供稳定帮扶照管,这些人除了是帮助个体,也是为国家、社会分忧解难,理应是喜闻乐见的良序风范,自然应当优先保障相关主体的权利资格和主张,真正体现好人有好报,以引导、鼓励良善和帮扶行为。
综上,笔者认为,在此类司法案件中,应当谨慎处理形成实质上的抚养、扶养、赡养、扶助等关系的其他非近亲属的“赔偿权利人”的主体资格认定问题。同时,在立法层面有必要更加体现公正合理性,进一步填补漏洞、完善规则。